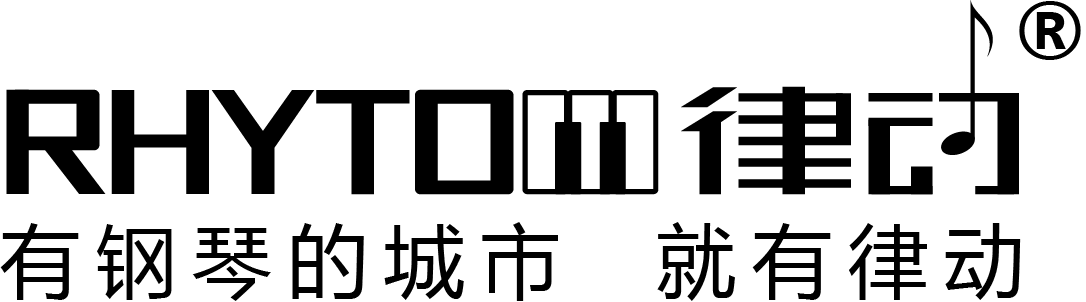1925年8月15日,奇科里尼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個音樂之家,自小被人視作“神童”。
8歲時,奇科里尼與意大利歌劇作曲家弗朗西斯科·齊來亞結緣。那時,齊來亞已是那不勒斯音樂學院領導,奇科里尼之母焦慮于兒子是否有音樂天賦,想方設法安排兒子與齊來亞見了一面。奇科里尼在齊來亞面前彈奏了足足四五十分鐘,直到他說:“轉過身來,不要再盯著琴鍵。” 齊來亞邊彈曲邊問奇科里尼聽到了哪些曲子和音符,奇科里尼對答如流,齊來亞隨即建議,“這孩子應該進音樂學院。雖然他的年齡比入學年齡(13歲)要小,但我會和學校領導爭取特例。”
奇科里尼能進入那不勒斯音樂學院,得益于實齊來亞的大力推薦。在那里,他跟著Paolo Denza學鋼琴彈奏,也在齊來亞的堅持下師從意大利鋼琴家亞歷山德羅·朗戈的兒子阿希爾·朗戈學作曲、和弦與復調。
和奇科里尼一樣,阿希爾·朗戈常年受哮喘折磨。齊來亞免不了要來代班,奇科里尼也因此有機會親得齊來亞教導。那時每天早上八點,齊來亞都會準時來到學院,站在那兒看學生來來往往,“他非常善解人意,即使是代課,也都把自己拾掇得非常優雅。”奇科里尼笑說,“你能想象一位寫出了《阿德里安娜·萊科芙露爾》、《阿萊城的姑娘》等歌劇杰作的大師會這么做嗎?”
16歲,奇科里尼開始在那不勒斯圣卡羅歌劇院表演。然而1946年以前,他也一度淪落到只能在酒吧彈奏為生。轉折出現于1949年。這一年,奇科里尼在巴黎的瑪格麗特·隆國際鋼琴比賽拿下首獎,落腳巴黎,國際巡演也接踵而至。奇科里尼去了拉丁美洲,1950年又來到紐約,與紐約愛樂樂團合作了成名曲——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
1969年,奇科里尼加入法國籍,開始了巴黎音樂學院18年的任教生涯。他的錄音專輯也先后斬獲法國唱片學術獎、《留聲機》雜志最高獎“年度唱片獎”(1976年)。1999年12月,為慶祝在法音樂生涯50周年,奇科里尼在巴黎香榭麗舍劇院舉辦了一場獨奏音樂會。
和很多藝術門類一樣,鋼琴界也慣以派系區分風格,知名的有俄羅斯學派、德奧學派和法國學派。奇科里尼是典型的“法國學派”,也很可能是他這一輩法國學派鋼琴家中僅存的最后一位,其演奏風格矜持、典雅、聲音層次豐富,富于歌唱性。
有人曾問奇科里尼會在什么情況下達至理想的工作狀態,他的回答是晚上。“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我應該出生在一個荒島上,但我的出生地那不勒斯卻完全相反。有時,我會刻意尋求孤獨。”他不太掛念生活中讓他不開心的事,而是全身心關注音樂,“晚上睡覺時,我常會思考如何改進指法上的細節,然后就會起床去鋼琴邊將這些揣摩付諸于指尖。萬籟俱寂之時,人會更容易,也更有耐心與自己相處。”他也并不自視為大師,而是將自己當成傳遞“接力棒”的使者,“再沒有什么比看到那些彈琴小孩的天賦像花一樣綻放讓人感動的事了。”
“老派”風格鋼琴家的代表
因為年輕時即移居求學法國,一直以來,奇科里尼亦以擅演法國作曲家的作品聞名。他的保留曲目名單中,有世人皆知的福雷、圣·桑、德彪西、拉威爾,也有名聲沒那么旺的夏爾-瓦朗坦·阿爾康、德奧達·德·塞弗拉克、埃馬紐埃爾·夏布里埃。但最出名的非薩蒂莫屬。
凡是彈奏過薩蒂作品的人,都知道這位作曲家愛給作品的演奏方式標注一些古怪指引,且專為演奏者而寫。比如,“給某某。我禁止任何人在彈奏作品時大聲讀出這些文字。無論誰斗膽違反我的指引都將引起我的憤慨。誰也不能例外。”再比如,“像一只牙疼的夜鶯在唱歌一樣”,“蠢狗在走路”,以表明“音色要嚴格控制”。
在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藝苗看來,科里尼是薩蒂作品的最佳詮釋者之一。時長7分多鐘,樂曲柔和惆悵的《裸體舞》(Gymnopedies)是薩蒂的代表作,“《Gymnopedie No. 1》的寥寥數音,給他彈出了一個漫長而溫柔的夢,不愿醒來。”而奇科里尼的薩蒂最吸引樂評人李嚴歡之處,在于他對音樂的敏感以及聲音層次上的明晰,“更可貴的是,他的演奏始終有一種古樸之美。雖然他的技術很全面,演奏時卻不顯山露水,全都化解于一種近似清純的琴聲中。越到晚年越是這樣,這才是最高明的技術。”
1950年代以降,以意大利鋼琴家莫瑞季歐·波里尼為代表的“現代”演奏風格在琴壇占據了上風,這一風格造就出的很多鋼琴家,演奏時始終將個性、情感隱藏于作品的結構、形式之后,“普遍風格更理性、冷靜、克制,什么都四平八穩,沒毛病可挑,卻也沒有記憶點。”
隨著五花八門的鋼琴比賽不斷涌現,這種現代風格變得更“模式化”,演奏者也愈發遵循既有模式,限制了自我個性的發展。
作為老一輩鋼琴家,奇科里尼的演奏風格和年輕人相比,更自由,給予音樂的空間和想象力更大,沒那么多“模式化”。李嚴歡感慨,我們為何懷念奇科里尼,或者說在他之前鋼琴演奏藝術的黃金時代?“主要是較之如今日趨客觀的演繹,那一時期的鋼琴家常透過對豐富的情感表現和色彩無盡變化的追求,彰顯出鮮明的個人魅力。有少數鋼琴家不排除有‘曲解’作品之嫌,但他們演奏時散發出的浪漫主義氣息,在現代鋼琴家中也很難聽見。”
其實在奇科里尼時代,鋼琴演奏者因參賽而成名也漸成主流,只是那時的比賽評委本身都是音樂大家,會以寬容之心樂見不同個性的選手,也明白怎樣的選手將來的路會走得更好更長。那個時代的比賽評委是選“音樂家”、“演奏家”,“現在的比賽卻是在選最好的‘參賽選手’,甚至是做交易、做買賣。再大的比賽都是一幫職業評委或鋼琴教授組成的利益集團,就像開飯店,大家輪流坐莊請吃飯,哪還有什么好結果?比賽名次早也不是經紀人看重的東西。”
和小提琴家到了60歲必然會走下坡路不同,鋼琴家更容易在琴鍵上留存青春。奇科里尼的演奏巔峰期亦長,而且是越到晚年越精進,幾近于“奇跡”。其實,他最為活躍的時期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從那時一直到去世前,奇科里尼始終仍代表著1850至1950年代鋼琴家那里承襲而來的‘老派’風格。”這種風格在1940年代后出生的鋼琴家里雖還有,但已是極少數。美國鋼琴家莫瑞·普萊亞、巴西鋼琴家尼爾森·弗雷里等現世最杰出鋼琴家,都是老派風格的繼承者。
現任教于上海音樂學院的青年鋼琴家薛穎佳2006年曾在比利時聽過一次奇科里尼的鋼琴獨奏音樂會,“在歐洲你會有很多機會聽大師的獨奏會,但他的音樂會是為數不多仍讓我記憶猶新的一場。”當時,奇科里尼剛做完一場癌癥手術,一般到他這個年紀,鋼琴家都會出現技術水平和記憶力的退化,“他的技術能力卻完全不輸年輕人,好像正當壯年,指尖干凈,音色漂亮變化多,完全游刃有余。”薛穎佳說,“一方面,這和他的天賦有關,另一方面也和他保持頻繁的演奏、練琴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