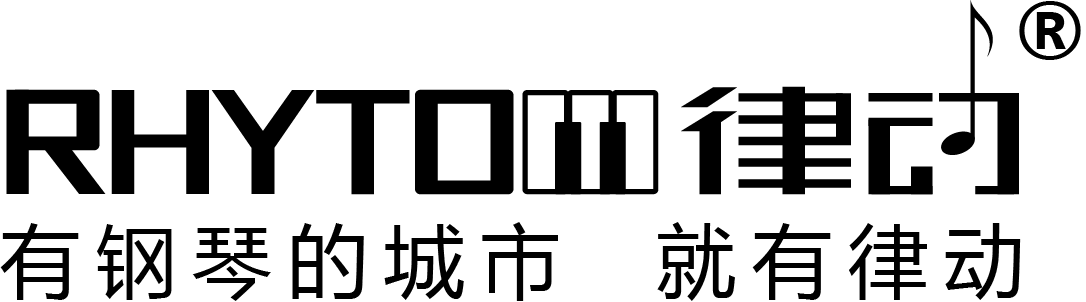大多數(shù)人,也許一生都無法體會到我每天在音樂中享受到的快樂,這個世界難以進(jìn)入,更難以脫開,因為它太美、太迷人了。這種樂趣難以描述,我只能用‘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來形容——傅聰
靠在沙發(fā)上,靜默,吸著煙斗,微微喘著氣。弟弟傅敏說,兄長白日練琴至天黑,睡了一覺,剛醒來,一群記者圍坐著,不敢出聲。此前大家都聽說了,老先生向來不喜歡接受采訪,尤其不喜歡談《傅雷家書》,因此不免有些惴惴。
在國人印象中的傅聰和真實的傅聰之間,也許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在《傅雷家書》中,傅聰韶華當(dāng)年,意氣風(fēng)發(fā);如今的傅聰,則是一個儒雅的紳士,是董橋筆下心儀的老派文人——在我們見面的那天晚上,他手持黑色的煙斗,一襲黑色的中式對襟棉衣,絲綢長褲和布鞋自然也是黑的;黑色的頭發(fā)梳成清爽而一絲不茍的發(fā)型,倒是兩抹長壽眉有些灰白,在眼角處轉(zhuǎn)個折,垂了下來。
只有那伴隨他幾十年的半指手套,提醒人們他內(nèi)心到底有多年輕——1972年,復(fù)測在奧地利音樂會前夕摔斷一根手指頭,此后一直患有腱鞘炎。為了保證血液流通,傅聰需要常年戴著手套取暖,即便在演出時也要戴著。我現(xiàn)在好像不戴手套都不會彈琴了!他笑著說。
關(guān)于成長:先為人,次為藝術(shù)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
2010年12月,他加盟國家大劇院紀(jì)念肖邦200周年誕辰的系列音樂會,并擔(dān)任第16屆肖邦國際鋼琴大賽的評委——那是他自1985年之后,25年來首次出現(xiàn)在該賽事中。
本屆大賽的冠軍尤里安娜-阿芙蒂耶娃恰好是傅聰大師班的學(xué)生。對此,老先生難掩一絲得意:我相信,我還是盡了一份力的!
父親傅雷曾要求傅聰,一定要先為人,次為藝術(shù)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如今傅聰年逾古稀,卻自謙道:我一輩子都沒有違背這個原則,可是,如果自稱是一個藝術(shù)家或鋼琴家,我覺得是夸夸其談,自己還沒有資格這樣說。
早在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時代》周刊就將傅聰列為封面人物。盛贊其為當(dāng)代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傅聰則說:我那一代得人,可以說是有家學(xué),如果說我跟別人有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就在這里。
1934年,傅聰出生于上海。起初父親想讓他師從黃賓虹、劉海栗等巨匠習(xí)畫,但見其對古典音樂有著近乎天賦的敏感和喜好,遂改而令其學(xué)琴。在《傅雷家書》中,讀者可以看到傅雷教子的嚴(yán)苛——為了保證傅聰每日數(shù)小時的練琴時間,傅雷把兒子從小學(xué)撤回,專門延請名師在家中教其英文、數(shù)學(xué)等科目,至于國文一科,則由自己親自選編教材,與以教授。鋼琴方面,先是請老朋友雷坦當(dāng)啟蒙老師,接著在傅聰9歲的時候,令其拜李斯特的再傳弟子、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為師。傅聰至今鼻梁上還有一道疤痕,那是因為小時候練琴走神,結(jié)果傅雷順手就拿了一個碟子朝他扔了過去,在臉上劃了一道口子,可見管教之嚴(yán)。
1948年,由于時局動蕩,傅雷一家曾遷往昆明,直到1951年,17歲的傅聰才重新拾起了終斷3年的琴藝,從此終生不渝。他自嘲這樣的年齡(學(xué)琴),真是前無古人。但他4年后的成功,證明年齡之說的虛妄:1955年3月,代表中國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的傅聰名列第三,這是中國人首次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尤為難得的是,他還斬獲了肖邦作品中演奏難度最大的瑪祖卡最佳獎。一個東方人,竟然如此貼切而深刻地再現(xiàn)了肖邦的靈魂,以至于演出結(jié)束后,具有很高音樂修養(yǎng)的波蘭觀眾如潮水一般向他涌來,擁抱我,問我,讓他們的淚水沾滿了我的臉;許多人聲音都啞了,變了,說他們一生從來沒有如此感動過,甚至說‘為什么你不是一個波蘭人呢’?
此后的數(shù)十年,傅聰始終被認(rèn)為是肖邦作品的最佳闡釋者之一,被稱為有分量的巨匠鋼琴詩人。
關(guān)于父親: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然而,對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傅聰之為人所知,并非因為他的琴藝,而是因為《傅雷家書》。
1954年,傅聰留學(xué)波蘭,從此與父親開始了長達(dá)12年的書信往來。傅雷在次年4月的一書,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聊八卦),而是把兒子當(dāng)成了談?wù)撍囆g(shù)的對手,同時也借此訓(xùn)練兒子的文筆、思想,并隨時給兒子做一面忠實的鏡子。
1981年,傅雷次子傅敏將百余封家書選編出版,一時間震動海內(nèi)。但對于當(dāng)事人來說,那些家書無疑超出了談藝錄乃至瑣碎的人生教條的意義,而具有那個特殊時代的意味。
在那12年中,傅聰由弱冠之年遠(yuǎn)赴重洋,中間經(jīng)歷了傅雷被劃為右派1958年傅聰叛逃英國1964年傅聰加入英國籍等中國風(fēng)波和事件。在某種意義上,那些家書更是傅聰羈旅英倫20余年,傅雷念茲在茲的遺書——1966年9月3日,自反右以來一直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傅雷,與夫人朱梅馥一起自盡。直到11月,傅聰才得知父母的死訊,可謂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1977年,傅聰在朋友吳祖強的幫助下,給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寫信,表示回國探親的懇切心情。1978年12月,鄧小平批示:傅聰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統(tǒng)一,由文化部辦理。自此,傅聰才真正得以重歸故里。
1979年4月,傅雷夫婦得到平反。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家庭都是傅聰不忍提及的話題,《傅雷家書》更是不忍重讀,因為一看到那些文字便會淚流面滿。他曾經(jīng)對記者說,我有一個朋友,他的祖父去世前,曾在一本宋詞集的扉頁上,給他留下過幾句話。在他祖父去世之后的兩三年里,他只要翻到那里,必定會痛苦。那么你想想,當(dāng)一個孩子看到整整一本情真意切的書信,而寫這些信的人卻已帶著那么多遺憾和痛苦離他而去時,他會是怎樣的感受?
直到最近幾年,他才稍微自我安慰說:假如放在身邊偶然看到,我會去翻一翻。但是,《傅雷家書》在我心里頭,我何必一定要去看呢?
關(guān)于音樂:都以朗朗為榜樣,不是好現(xiàn)象
即使是成名之后,傅聰也一直保持著苦修者一般的練琴強度。每天上午10點半練琴至下午5點,中間不吃午飯,只為了讓琴聲連貫。到了演出前的一兩天,更是要保持8到10個小時的練習(xí)時間。夫人卓一龍就經(jīng)常說他:哪有這么練琴的!練琴應(yīng)該有所保留,不要全部拿出去。可是對我來說,每天要打到我認(rèn)為的極致才可以,所以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其實,卓一龍自己也是一個鋼琴家。傅聰家里有5 架鋼琴,現(xiàn)在只有夫妻兩人彈了。我們各自有琴房,平時只在早晚吃飯時見面,家里有傭人,雜務(wù)都不必操心。我夫人有時做些園藝,她那片玫瑰園就在我琴房的窗下。傅聰說。他們疏于社交,也極少出席名流宴會。只有在天氣好的時候,夫婦倆才會一起出門,開上20分鐘的車道牛津大學(xué)校園散步。
他的兩個兒子成長在這個音樂世家(長子是與第一任妻子、大音樂家梅紐因的女兒彌拉所生),但都沒有選擇練琴這個苦差事,他們甚或調(diào)侃父親是一個怪老頭。但傅聰說:我對名利看得很淡,錢后面加幾個零,對我來說是很空洞的事情。在音樂乃至音樂之外,天天學(xué)到一點新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一種享受。
最近幾年,傅聰受上海音樂學(xué)院的邀請,每年抵滬教兩個月的大師班,學(xué)生中既有小、中、大學(xué)生,也有也已成名的鋼琴家。他發(fā)現(xiàn),小學(xué)、中學(xué)的學(xué)生非常有才年,遠(yuǎn)遠(yuǎn)高于大學(xué)部得人;此前他也直指中國學(xué)生不缺才華,但沒有文化,因為很少看書,對樂器之外的音樂體悟太少,獨立思考在這里至今也還是個理 想。
他批評中國社會急功近利,學(xué)琴的人以為把手指練得飛快,就會變成第二個朗朗。我對朗朗是很佩服的,他是一個鋼琴天才,可是,以他作為榜樣,不是一個很好的現(xiàn)象。他甚至預(yù)言,大批的孩子學(xué)琴,5到10年之后,中國只不過多了一批光彩的手指而已,這與做人、做藝術(shù)家的境界,相去甚遠(yuǎn)。
在一些人看來,傅聰是神秘的,他回應(yīng)道:大多數(shù)人,也許一生都無法體會到我每天在音樂中享受到的快樂,這個世界難以進(jìn)入,更難以脫開,因為它太美、太迷人了。這種樂趣難以描述,我只能用‘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