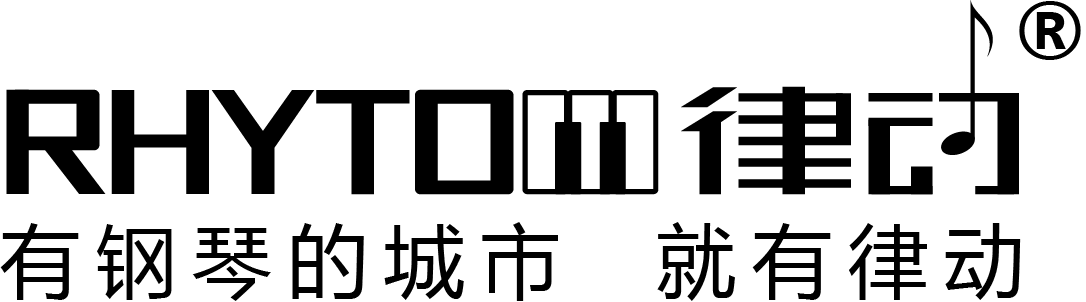談到我的成長,不得不提我的恩師凌遠教授,因為我的鋼琴基礎(chǔ)、我對音樂最初的認知都是她給的。從7歲到14歲出國前,我一直跟她學習,當然有時周廣仁先生也會給我一些指點。我的手比較細長,凌老師因此在技巧方面很注重培養(yǎng)我對聲音的直覺,在觸鍵發(fā)力上對自己肢體自制能力的把握,從而形成我現(xiàn)在特別通透的音色。我悟性很好,一點就有,所以經(jīng)常凌老師一點我就通了,師生間特別默契。直到現(xiàn)在,每次回國,我都像回家一樣去她那上上課,聽聽她的指點心里總是很踏實,畢竟她最了解我和我的音樂。我特別怕別人限制我的演奏,但小的時候,肯定都是從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經(jīng)典作品一部部彈出來,當時凌老師箍得也比較緊,但現(xiàn)在都比較順著我的風格,對我的處理都很支持。我很感謝凌老師從小培養(yǎng)了我對音樂的敏感,這使得我出國后,有能力靠自己完成對所有作品的理解和詮釋,獨立處理、判斷所有的演奏。這其中經(jīng)常沒有對錯,只要自己覺得對,就自己說服自己然后再用演奏說服觀眾。
這也許正是王羽佳與很多國內(nèi)從小到大在按部就班一對一嚴謹教學環(huán)境下成長的鋼琴天才最大的不同,很小就已經(jīng)獨立地開始舞臺演奏的實踐。在美國,她遇到又一位恩師格拉夫曼。而格拉夫曼給予王羽佳最大的影響,不僅在課上,更多來自觀摩大師的音樂會演奏,其中得到的收獲遠遠大于在課上的學習。
與王羽佳合作的所有著名指揮家,幾乎都是她的長輩級甚至隔代的輩分關(guān)系,他們的年齡和經(jīng)歷都和音樂的發(fā)展一脈相承,留下傳統(tǒng)音樂的浸潤。而在19歲就開始與之愉快合作的迪圖瓦大師,給26歲的王羽佳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影響。王羽佳說:迪圖瓦雖然已經(jīng)77歲,但心態(tài)很年輕。他是真正從傳統(tǒng)走過來的,所以與他合作是一件特別幸運的事。我們有時也會討論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區(qū)別和關(guān)系。現(xiàn)在社會信息發(fā)達,生活節(jié)奏快,收獲手段先進而便捷。但迪圖瓦大師說:我們那個時代都是用手寫情書,一封信的來往要幾個星期,人在漫長的等待中發(fā)展了情感。時間使人的情感沉淀得更深厚,因此傳統(tǒng)的生活節(jié)奏和方式與人性更接近。
也許正因為與無數(shù)大師的心靈交匯,性情浪漫無羈的羽佳,仍然能將自己年輕的激越生命融入醇香濃郁的經(jīng)典音樂,沉醉揮發(fā),更富光彩。只是,她對舞臺演出的渴望遮掩不住一個藝術(shù)家強烈的表達欲望;而巴赫 ,更適合舞臺下留給自己彈奏,成為滋養(yǎng)內(nèi)心的一種內(nèi)省與安撫。
我喜歡演出,想演出。但我的舞臺表達欲求,完全出自對音樂誠懇的熱愛。我在舞臺上從來沒有職業(yè)鋼琴家的概念,也無所謂觀眾的反應。但我相信自己如果特別投入,特別用心的演奏,一定會感染和感動觀眾。我想我之所以成功,也許除了天分,勤奮、毅力和機遇外,對音樂真誠地喜愛,應該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對音樂理解的悟性和富有靈性的創(chuàng)造性,對新事物不斷追求的好奇心,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