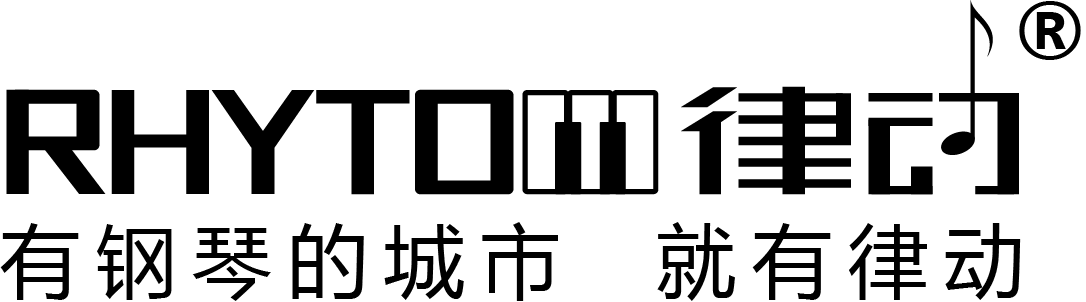6月20日,法國Esprit鋼琴音樂節在廣州星海音樂廳舉行。該音樂節源自法國波爾多,意在不遺余力發掘鋼琴界新星。更好的思想產生行動力是音樂節的創始愿景。作為音樂節的開幕式領銜演奏嘉賓,26歲的旅美青年鋼琴家元杰演奏了浪漫主義鋼琴詩人肖邦的24首前奏曲。這24首前奏曲風格迥異、各成一格,元杰一氣呵成地將作品中其極其敏感的情感、豐富的變化傳達給了聽眾。在元杰看來,這24首前奏曲表現了人類情感細膩深刻之微末:語言走到盡頭、描述不了的時候,音樂才緩緩地開始,緩緩地道來。
元杰早年畢業于廣州星海音樂學院附中,目前在美國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以全額獎學金的身份攻讀最難的最高演奏博士文憑。該學院的演奏博士學位,一年只錄取零至兩人,是全球公認的最難學位。
頭發微微蜷曲,戴著黑框眼鏡,說話輕快,個性活潑,舞臺下的元杰看起來就像鄰家大男孩。但他已經在世界全部五大洲的超過一百座城市舉行過鋼琴演奏會。從22歲起,就陸續被國內外數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或榮譽教授。
元杰自稱是不稱職的音樂家:我每天練琴五個小時,一天多半的時間,都不是在鋼琴旁邊度過的。元杰愛好廣泛,喜歡話劇、馬術、電影、寫作和畫畫,最近還打算學開飛機。元杰認為音樂是從各種各樣的文化養料和藝術土壤中出生的,因此不能只讓自己在一盤完美的盆景面前學習如何栽種,而是應當去自然中、社會中、去所有的學科中來感受和培養自己的音樂素養。經歷國內外兩種學習環境,在元杰看來,外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在對音樂價值追求上有很大不同:為了學音樂而學音樂和因為熱愛音樂而學音樂,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久前,元杰剛剛在最頂級的意大利布索尼(Busoni)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是繼中國鋼琴家陳宏寬、沈文裕、吳牧野之后,第四位獲獎的中國鋼琴家。這次比賽令元杰印象深刻的,并非獎項本身,而是一個波蘭評委拉辛斯基在頒獎禮上說的話:如果你覺得贏了今天的比賽,就代表著你比昨天彈得更好了,那你就錯了。獎項并未改變演奏者本身的水平,元杰對比賽、音樂本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音樂是完美的,但比賽不是。比賽和音樂不是畫等號的。如果你熱愛音樂,那么就不要在乎比賽的結果,如果你熱愛比賽,well,那么你可以轉行當街頭斗琴的人。
作為長期致力于音樂推廣和普及的青年音樂家,元杰對這次法國Esprit鋼琴音樂節首次落戶廣州很看好。該鋼琴音樂節與世界最有名望的鋼琴比賽—伊麗莎白女王音樂比賽以及法國最早專注于鋼琴的音樂節的雅各賓音樂節聯合,致力于推廣世界各地年輕有為的鋼琴家:"法國Esprit鋼琴音樂節"為年輕音樂家們提供了一個國際藝術交流的新舞臺,一個青年藝術新星培養平臺,一個開放的年輕鋼琴家的節日。尤其是在中國,類似的音樂交流平臺比較少,這給了國外年輕音樂家與中國聽眾交流的機會。
時代周報:中國的鋼琴熱持續了很多年,但成功只屬于少數人。你對徘徊在堅持與放棄之間的這些人有什么建議?
元杰:首先,我絕不敢稱自己是已經有成就的鋼琴家,我真的還只是鋼琴領域里面的一個小學生。但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名鋼琴家,最不應當追求的就是功利思想,例如要成名成家,要世界著名,要萬人矚目。一個真正成熟的鋼琴家應當在一個相對寂寞和孤獨的狀態里,沉浸在沒有絲毫雜念的音樂中,苦行僧般地去生活在音樂世界里,一點一點地深入進去、一步一步地發現更多的美。成為鋼琴大師的只有少數人,這是由客觀條件和先天天分決定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莫扎特。我常說:音樂家最大的幸福,不是有多少粉絲有多少音樂會,而是在古典音樂中感受一般人無法感受的極致的美和最高的情感表述。這幸福不是金錢能買到,也不是名望能換來的。當我們靜下心,拋開所有雜念去感受和演奏音樂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是如此的幸運,能夠在勃拉姆斯、巴赫、莫扎特、馬勒等所有大師的音樂中感悟到世間的最情感和宇宙的最透徹。
時代周報:你正在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攻讀博士文憑,在有沒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時刻?
元杰:我現在讀的是茱莉亞音樂學院的最高演奏博士文憑。茱莉亞音樂學院有兩種博士文憑:最高演奏博士文憑、音樂學博士。音樂學博士,就是我們國內通常說的博士文憑,要寫論文、過答辯。而最高演奏博士,是基于演奏的水平而選取的,沒有論文和答辯,但是硬性規定了一年開音樂會的數量和質量。在茱莉亞音樂學院,音樂學博士每年招收5-7人,而最高演奏博士則只招收1-2人,有時候甚至不招收。這并不是說孰重孰輕,而只是說這兩種博士的側重點完全不一樣。畢竟我們社會需要的是更多的高水平的教育家(音樂學博士)和少量的演奏家(演奏博士)。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種設置,中國的大學也可以學習這種系統。畢竟,這是一套互相補充、相輔相成的博士系統,沒有好的教育家,就不會有好的演奏家。沒有好的演奏家,就沒有辦法表現教育家的成果。
時代周報:美國的學習環境和中國相比,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元杰:我在茱莉亞音樂學院感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看到了外國學生和中國學生之間,在對音樂價值追求上的不同。可以說,整個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預科學院(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國琴童和韓國琴童。而在碩士和博士班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歐洲和美國人。我常常想,這些琴童最后都去了哪里?為什么少年天才卻很少有人攀上了更高的山峰?我覺得有兩點。第一,很多中國琴童是為了學音樂而學音樂,而多數的外國琴童是因為熱愛音樂而學音樂。一群中國學生在一起,討論的最熱烈的話題就是去參加哪個比賽能得獎,怎么樣能找到捷徑早點把曲子練出來。而多數的外國學生在一起,討論的通常是肖邦在這個地方為什么要用一個顫音,有什么意義,抑或是他被某個音樂家的作品感染得淚流滿面,而讓他無比難忘。第二點,很多中國琴童沒有獨立的思考能力,過度依靠老師。而西方的教學恰恰是平等教學,老師和學生互相啟發、互相研究。
時代周報:能向我們介紹三個你認為最重要的事物或者代表性的東西嗎?
元杰:中國有太多的東西可以介紹給世界,如果只能選擇三個,我會選擇:圍棋—它能代表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和中國人在社會博弈中的態度;唐詩宋詞—代表中國人偉大的漢語語言,以及對美的最透徹的感受和對文字的最智慧的運用;美食—代表中國歷史的傳承,以及統一和多樣并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