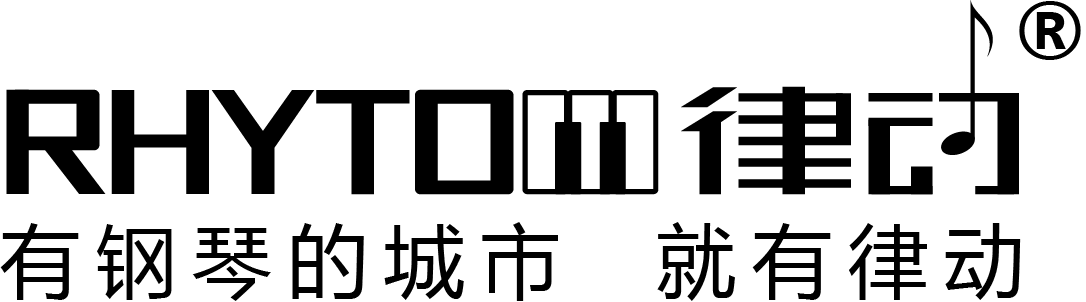肖邦與中國
1954年1月17日,翻譯家傅雷一家人到上海火車站送傅聰赴波蘭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次日晚,傅雷開始給傅聰寫家書,《傅雷家書》中,肖邦是出現(xiàn)得最多的音樂家。在傅雷父子的書信往返間,肖邦仿佛就是一位生活在他們當(dāng)中的親人。
傅聰獲得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后,漸漸享譽(yù)國際樂壇。1966年,政治的暴風(fēng)驟雨來臨,傅雷夫婦一起含恨棄世,留在國外的傅聰則背上叛國之名。這一家人的名譽(yù)要在十幾年后才得以恢復(fù),《傅雷家書》在中國也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名著。
歐洲樂評人曾以鋼琴詩人為題評論傅聰演奏的莫扎特與肖邦的鋼琴協(xié)奏曲:許久以來,我們未曾聽到過這樣的觸鍵,使鋼琴能顯出最微妙的音質(zhì)層次。在傅聰?shù)乃枷肱c實(shí)踐中間,有一股靈感,達(dá)到了純粹的詩的境界。他在琴上表達(dá)的詩意,不就是中國古詩的特殊面目之一嗎?他鏤刻細(xì)節(jié)的手腕,不是使我們想起中國畫冊上的畫嗎?傅聰則說:我覺得,肖邦呢,就好像是我的命運(yùn),我的天生的氣質(zhì),就好像肖邦就是我。我彈他的音樂,就覺得好像我自己很自然地在說我自己的話。
在中國,感覺自己的命運(yùn)與肖邦緊緊相連的不只是傅聰一家。單以鋼琴家而言,李云迪和郎朗就仿佛與肖邦心心相印。李云迪曾是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的最年輕冠軍得主。郎朗在波蘭成功演出之后,被當(dāng)?shù)孛襟w稱為長著中國眼睛的肖邦。以色列鋼琴大師阿里·瓦迪說:中國人與肖邦天生親近,中國人是最熱愛和最適合彈奏肖邦音樂的民族之一。
2010年,肖邦誕生200周年。世界古典音樂界無疑會(huì)成為肖邦年。中國是世界上除了波蘭之外最隆重紀(jì)念肖邦的國家,肖邦熱早在2009年就開始預(yù)熱了。傅聰、李云迪、郎朗都有演繹肖邦音樂的重要演出,全中國紀(jì)念肖邦200周年誕辰的音樂會(huì)將此起彼伏,初步統(tǒng)計(jì)不下200場。上海世博會(huì)期間,波蘭還將自己的國家館命名為肖邦館。屆時(shí),館內(nèi)每天都將舉辦肖邦鋼琴演奏會(huì)。
肖邦與祖國
古典音樂迷辛豐年(著有《樂迷閑話》)和鯤西(著有《聽者小札》)不約而同地說:肖邦雖然短命,但在音樂史上足以不朽!
關(guān)于肖邦的生日,現(xiàn)在存在兩個(gè)版本,一說是真實(shí)生日1810年2月22日,另一說是官方生日1810年3月1日。肖邦生于波蘭首都華沙郊區(qū),父親原籍法國,是華沙一所中學(xué)的法語教師,后來開辦了一所來華沙學(xué)習(xí)的外省貴族子弟的寄宿學(xué)校。母親是波蘭人,曾在一個(gè)貴族親戚的家庭中任女管家。肖邦7歲即能寫樂譜,8歲開始公開演奏,1826年中學(xué)畢業(yè)后入華沙音樂學(xué)院學(xué)習(xí),同時(shí)開始創(chuàng)作,很早已是一位聲名遠(yuǎn)播的天才音樂家。
那個(gè)時(shí)代的波蘭多災(zāi)多難。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個(gè)強(qiáng)國對弱小的波蘭進(jìn)行了三次瓜分。1830年11月2日,20歲的肖邦告別了親人,離開華沙出國深造,師友們向他贈(zèng)送了一只盛滿祖國泥土的銀杯。波蘭詩人維特維茨基在給肖邦的信中寫道:你只要經(jīng)常記著,民族性,民族性,最后還是民族性……正像波蘭有祖國的大自然一樣,也有祖國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內(nèi)在的、祖國的音響,雖然并不是每一顆心都能聽到它的聲音。肖邦12月初在維也納得知華沙爆發(fā)起義,他為未能參加這次起義而焦急,曾想返回波蘭參加斗爭,被友人勸阻。次年初在赴巴黎途經(jīng)斯圖加特時(shí)得知起義遭沙俄鎮(zhèn)壓、華沙陷落的噩耗,肖邦的精神受到強(qiáng)烈震撼。他曾寫道:我還在這里,我不能決定啟程的日子。我覺得,我離開華沙就永遠(yuǎn)不會(huì)再回到故鄉(xiāng)了。我深信,我要和故鄉(xiāng)永別。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
終其一生,國恨家愁影響了肖邦的音樂創(chuàng)作。音樂史家認(rèn)為:肖邦音樂的思想反映了歐洲資產(chǎn)階級民族運(yùn)動(dòng)總潮流的一個(gè)側(cè)面,喊出了受壓迫受奴役的波蘭民族憤怒、反抗的聲音。肖邦的音樂具有濃厚的波蘭民族風(fēng)格,對民族民間音樂的態(tài)度非常嚴(yán)肅,反對獵奇,同時(shí)又不被它所束縛,總是努力體會(huì)它的特質(zhì)并加以重新創(chuàng)造。
音樂史家將肖邦的創(chuàng)作分為華沙時(shí)期(1830年前)與巴黎時(shí)期(1831-1849)。在巴黎,肖邦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很快就名揚(yáng)四海。據(jù)說,最早是李斯特慧眼識英雄,把肖邦引進(jìn)了巴黎的沙龍。當(dāng)時(shí)流傳著一句名言:李斯特讓所有的鋼琴家黯然失色,除了鋼琴大師肖邦。
盡管在巴黎得到了榮耀與愛情,肖邦始終不能忘懷自己的祖國波蘭。一直到1849年,39歲的肖邦受盡了身體和心靈的折磨,在巴黎去世。臨終前,他對姐姐說:請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我要長眠在祖國的地下。
肖邦與喬治·桑
肖邦的一生,華沙和巴黎的生活各占一半。而在巴黎的時(shí)代,肖邦幾乎被喬治·桑占有了。
喬治·桑是一個(gè)頗不簡單的女人。她比肖邦大6歲,行為驚世駭俗:與丈夫分居,棄家出走到巴黎,不久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名世。雨果說:她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具有獨(dú)一無二的地位。特別是,其他偉人都是男子,惟獨(dú)她是女性。
喬治·桑帶著兩個(gè)孩子定居巴黎后,身邊經(jīng)常圍繞著許多追隨者。在別人的眼里,喬治·桑只有1.54米高,抽雪茄、飲烈酒、騎駿馬、穿長褲,終日周旋于眾多追隨者之間。當(dāng)有人批評喬治·桑不該同時(shí)有四個(gè)情人時(shí),她回答:一個(gè)像我這樣感情豐富的女性,同時(shí)有四個(gè)情人并不算多。
在肖邦傳記中,他與喬治·桑的愛情總是被戲劇化地渲染一番。
喬治·桑第一眼就對肖邦產(chǎn)生了興趣。肖邦卻沒有對她一見鐘情,他甚至對朋友說:那個(gè)喬治·桑是令人討厭的女人,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女人,我非常懷疑這件事。此時(shí)喬治·桑與詩人繆塞剛剛分手。她對男人了如指掌,肖邦是一個(gè)男子,卻有女性氣質(zhì),體質(zhì)柔弱,憂郁傷感,此前的兩次失戀使他懷疑女人的情感,又無法擺脫對愛情的渴望。在喬治·桑的強(qiáng)攻之下,肖邦的感情防線很快就崩潰了。無論外人如何評價(jià)這段愛情,肖邦畢竟在這時(shí)迎來了另一個(gè)創(chuàng)作的高峰。
辛豐年不無深意地寫道:‘鋼琴詩人’的寫作生涯,在喬治·桑這位浪漫派女作家筆下被浪漫化了。她說什么,肖邦過于追求完美,總是改了又改,每寫一頁要耗上整整一星期的時(shí)光。說什么肖邦冥思苦想,嘔心瀝血,有時(shí)苦惱于筆不從心,竟會(huì)撕扯自己的頭發(fā),哭了起來,甚至將手中鵝毛筆一折兩段。然而雖然反復(fù)涂改,終于還是恢復(fù)原稿。其實(shí)從手稿上來核實(shí),并不能證實(shí)她這些記述。
肖邦喜歡安靜,喬治·桑卻是生機(jī)勃勃。她曾稱他:我親愛的尸體。在別人記載中,喬治·桑的莊園里接待過的名人不計(jì)其數(shù),包括音樂家肖邦和李斯特、詩人繆塞、文學(xué)家福樓拜、梅里美、小仲馬和巴爾扎克等,還包括拿破侖的小弟弟熱羅姆·波拿巴親王。值得玩味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她龐大的情人隊(duì)伍中的一員。
肖邦和喬治·桑共同生活9年之后,不得不分手。此后,肖邦再也沒寫出重要的作品,臨終時(shí)說:我真想見她一面。而喬治·桑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愛情仍在進(jìn)行著,不斷有作品產(chǎn)生。喬治·桑一生長壽而且著作等身。
肖邦與時(shí)代
辛豐年說,肖邦所生的時(shí)代,是世界音樂名人輩出的時(shí)代,像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產(chǎn)生大畫家一樣,可謂一時(shí)多少豪杰。與肖邦并世齊名,同樣與鋼琴結(jié)下不解之緣的作曲家兼大演奏家是李斯特。肖邦忠于一己,只表現(xiàn)自我,而且連這也深自矜惜,不喜賣弄。相反,李斯特是極愿將自己的才氣向廣大聽眾宣示無遺的。辛豐年認(rèn)為,有些人不喜歡肖邦的作品,但是肖邦肯定不朽。同時(shí)代的競爭對手李斯特就很難說了,顯然,他比不上肖邦。
肖邦所生活的巴黎時(shí)代,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黃金時(shí)代。肖邦在巴黎結(jié)識了不少音樂大師,但是他不想成為鋼琴家,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鋼琴家意味著用各種的表演技巧來取悅聽眾,爭得名利。肖邦甚至說:這里有最輝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偉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惡。每一個(gè)行動(dòng)和言語都和花柳有關(guān);喊聲、叫囂、隆隆聲和污穢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這個(gè)天堂里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說誰也不過問一個(gè)人是怎樣生活的。盡管音樂的天才使肖邦名利雙收,他卻不快樂。
在音樂史家看來,肖邦在華沙是愉快、開朗的,這一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基調(diào)是樂觀的,但思想深度卻有限。肖邦在巴黎的創(chuàng)作很快進(jìn)入成熟期,音樂所表現(xiàn)的,一方面是對祖國興亡的緬懷與思念,一方面是他在巴黎的生活與愛情。傅聰認(rèn)為:肖邦很自我,個(gè)人的痛苦與喜樂都非常重要,他在音樂中把這些情感夸張到最大,不過肖邦的靈魂非常熱情而且有深沉的哀痛,但是沒有一點(diǎn)感傷或是無病呻吟的味道。
在鯤西看來,傅聰始終不忘他父親的教誨: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shù)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后才是做鋼琴家。有文化、有修養(yǎng)和有思想,這樣彈琴就一定有品位。李云迪是詩人,浪漫主義作品或許更適合他,特別是肖邦的。郎朗則是活力超常的鋼琴演奏家。在肖邦身后的一百多年來,每一位音樂家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來演繹肖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