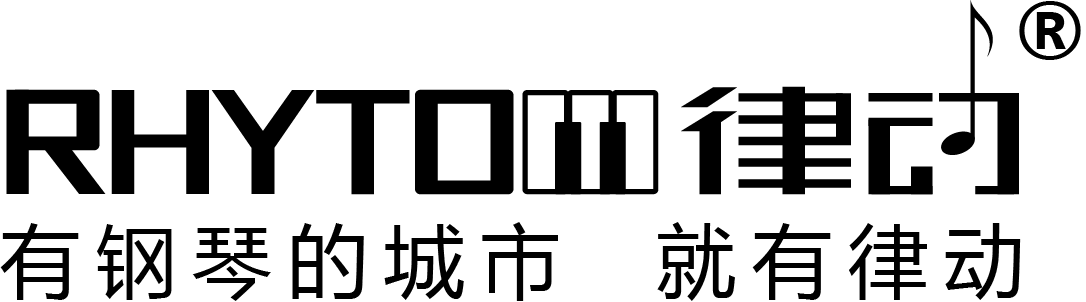對古典音樂愛之越深,我們越能體會到古典音樂演奏家的可貴!這是個異常艱辛的行業,競爭異常的激烈,即使最終成了名,也成不了經濟上的暴發戶。所以,對于每一個留名史冊的音樂家、演奏家,我們都應該抱著敬仰和尊重的態度,今天波蘭鋼琴演奏家阿圖爾·魯賓斯坦以其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和眾多高品質的錄音作品躍然于我們眼前,他的那句名言我永遠不怕犯錯,甚至要錯就徹底去錯,那些萎縮不前害怕體驗,害怕犯錯的人,他們講不出情感,干不出樂趣。凸現出他卓爾不凡的鮮明個性。
來自肖邦故鄉的魯賓斯坦,他在演繹肖邦作品時,與其說是在演繹肖邦,還不如說他是借肖邦的音符表達自己對故鄉的眷戀!從這一點看,魯賓斯坦的演繹確實要比別人多一份坦然。指揮家、鋼琴家巴倫博伊姆曾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評價魯賓斯坦的演出的:是魯賓斯坦讓我了解了肖邦。他開場常彈的一首曲子是肖邦的F小調幻想曲,他高貴、宏大的演奏風格與當時流行的像患了結核病似的病態、感傷的肖邦演奏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魯賓斯坦的處理非常有陽剛之氣,他彈出了音樂的高貴與宏大,我找不出更好的詞來形容。
魯賓斯坦第一次見到約阿西姆的時候,還不滿四歲,而家人真正決定送他去柏林學習時他已經11歲了,對于一個有如此音樂天賦的孩子來說,浪費的時間刻真是不少了,盡管如此,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魯賓斯坦已經充分了解自己的天賦是大有可為的,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的與眾不同,知道自己能做很少有人做得了的事,做那些能為自己帶來獎賞的事,從親吻、喝彩到巧克力,繼而獎賞的回報形式變成了使他進入高層社會核心圈子的通行證,使他成為同行們羨慕不已、譽滿全球的名流人物,同時也帶來了巨額財富。確切地說是魯賓斯坦自作主張離開了巴爾特,他的老師巴爾特是一個固執而認真的人,他要求他的年輕學生必須全身心地努力練習,非常嚴格,與魯賓斯坦師出同門的鋼琴家肯普夫曾生動地形容這位老師為東普魯士的老巨人,說他是一位老套守規的音樂教師,一位脾氣很壞,卻有一顆金心的監工。而魯賓斯坦與巴爾特的矛盾在哪呢?在巴爾特的嚴格指導下,三年的用心學習終于結出碩果,但年輕的魯賓斯坦不愿再按部就班地發展,不愿最終成為一名教師,他渴望奪取新的勝利,于是在17歲的時候,魯賓斯坦結束了正規的音樂教育,開始了他想要過的生活。
魯賓斯坦的個性中混雜著一些復雜奇怪的特征,那些矛盾重重籠罩在他的生活中,在一些事例中也許能說明問題,比如說,魯賓斯坦對自己超常的天賦感到自豪,但在培養發展自己天賦方面卻不特別勤勉;他相信自己的音樂才能,但對自己是否能獨立發展,缺乏信心;他決意要減少和父母的接觸往來,但對他們卻充滿了內疚感;他因能俘獲比自己大一倍的女人而興奮愉悅,但卻因不能博得同齡女性的歡心而困擾不安;他時常出入中產階級的上層人家,但卻因自己經濟窘迫而覺得羞愧。然而所有這些難題都未能讓他退卻,他最終還是克服了其中的一些困難,但由此而起的副作用則永遠留在他的身上。
音樂界一般把1900年在柏林的演出定為魯賓斯坦的正式首演。這場音樂會由約阿西姆指揮,魯賓斯坦演奏了圣桑、莫扎特以及舒曼、肖邦的作品。此后的十幾年里,他相繼在德國、波蘭、法國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很多國家巡演,然而他卻沒有得到和他的天才相匹配的聲望。魯賓斯坦了解自己的這種狀況,也知道其中原因。雖然他曾同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相處過一段時間,但從巴黎首演開始,他就已經拋棄了少年時所受的正規鍵盤演奏法。天賦助他掌握并演奏了大量充滿靈氣和活力的曲目。但是由于他缺少鋼琴大師的指導,詮釋出來的作品未免古怪,甚至粗糙,出眾的技巧也不太穩定。
關于魯賓斯坦的享樂主義,年少時可能是比較突出,天才的不羈時常有所流露。最典型的例子是夜夜歡歌,從不練琴,時常他走上舞臺前還會問工作人員:親愛的,你肯定今晚的節目是這些嗎?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魯賓斯坦便收起了浪子情懷,全身心的將自己的才華和熱情投入到音樂中。但是那種享受生命的感覺還是時時在他的音樂中體現出來,不過就如同他自己的那句名言所示:音樂家沒有最好的,他們都有自己的特色。無論演奏家們如何演釋某一作品,他始終不會超出音樂本身基本的內涵,始終只會演奏那些音符和節奏,絕不會有本質上的錯位。魯賓斯坦只需要盡情發揮他的特色便可以了。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后總是有一個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不知道這話對于魯賓斯坦來說是不是老生常談,魯賓斯坦的風流韻史幾乎和他的演藝生涯一樣長,雖然在一次采訪中,他曾發出過這樣的言論:我所有的女人,我夢寐以求的可愛女人,我都喜歡,自然界中異性相吸的特征在我身上表現得非常強烈,但婚姻的念頭令我恐懼,如果有朝一日你聽說我已結婚成家,那么我一定是瘋了……但最終他還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這并不代表他本著一顆回歸的心,他的生活依舊豐富多彩,絢麗多姿。
魯賓斯坦第一次到美國演出是在1906年,那時他還不滿19歲,對于這位年輕的演奏家,當時美國公眾的反映并不是很熱烈 ,不了解行情的魯賓斯坦似乎觸犯了某些禁忌,美國的媒體對他的評論毫不留情,他們說:魯賓斯坦的音色中很少具有溫暖的美感,而且他的演奏效果也幾乎沒有變化……加演曲目,一首純粹賣弄的作品……為什么是這樣的結果呢?后來一位音樂傳記作者分析說:魯賓斯坦的炫技性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他是勃拉姆斯、約阿西姆和巴爾特等反戲劇性音樂學派人物培養的弟子,他自然的分句手法,與已征服美國公眾、風格更加隨意流暢的浪漫主義大師相比,被認為是沒有詩意,這個打擊曾一度讓魯賓斯坦消沉。
晚年的魯賓斯坦,護照上是美國公民,大部分時間住在巴黎。他音樂生涯開始的地方是德國,但是,自1914年以后,他從不在德國舉行演奏會。他說:眾所周知,這是一段很可悲的歷史。人們可能認為我還抱著一顆極端的報復心理。可是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我一直熱愛著我的勃拉姆斯、我的貝多芬、我的莫扎特,以及我的席勒、我的歌德和海涅。對于誕生這些人物的國家,又是我在那里度過漫長歲月的國家,我怎能抱著一顆憎惡或報復的心去談論它呢?不,這樣的事,是絕對做不出來的。我只是對于死去的同胞,抱著非常的敬意而已。如果我再到德國去,我的那些死去的同胞.將會做什么樣的想法呢?
步入顛峰的魯賓斯坦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演出重心由歐洲轉移到了美國。1941年,他和小提琴家海飛茲,大提琴家費爾曼組成了鋼琴三重奏團,灌錄了貝多芬,舒伯特及布拉姆斯的鋼琴三重奏曲,這個搭檔,被稱為百萬三重奏,或卡薩爾斯黃金三重奏團在世,可惜的是,第二年費爾曼就客死美國,三重奏團只得暫時停止演出或錄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皮亞蒂戈爾斯基繼續擔任大提琴的部份,繼續進行錄音,維持了百萬三重奏的美譽。這樣的團體之所以令人欽佩,并不是因為組織成員都是當代演奏大師,而是這三位大師都能摒棄自己的成見,百忙中抽空練習,在經過彼此溝通后,演奏里掩飾了自己的光芒與個人特色,力求整體表現的完美。也許,此刻他們所表達的已不只是彼此間的默契,而是對作品更高境界的見解了。
在戰爭年代,歐洲許多優秀的指揮家都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他們為美國管弦樂開創出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所熟知的指揮家,像比徹姆、托斯卡尼尼、明希、巴比羅里、還有斯托科夫斯基、喬治·塞爾、庫謝維茨基等等他們都非常喜歡與魯賓斯坦合作,這不僅因為他出類拔萃的演奏,還因為他易于共事,當然也有例外的,魯賓斯坦與弗里茨·萊納就是水火不容,當年他們曾在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過好幾次,后來他們發生了爭執,據說是萊納含沙射影地說了肖邦的壞話,這讓視肖邦為偶像的魯賓斯坦大為發火,他幾乎掀翻了桌子,但據可靠消息說魯賓斯坦和萊納的絕交,源于一次錄音,魯賓斯坦的認真和萊納的不友好態度使矛盾激化,萊納的一句:我們不給獨奏家加班。,讓兩位著名的音樂家從此斷絕了合作的機會。
毫無疑問,魯賓斯坦演奏肖邦的作品是空前絕后的珍品。他把肖邦的個性完全融入演奏中,又把它彈得飽滿充分,他的健康自我與憂郁柔弱的肖邦達到了一種平衡和諧,然而魯賓斯坦又是一派逍遙,年少時荒唐地揮霍青春,與美女,雪茄和酒精為伴的經歷并未損害他到的健康,反而在花甲之年悠然灌錄唱片。看著他坐在長椅上,怡然自得地抽著雪茄的照片,讓人不禁猜想他對肖邦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懷。在魯賓斯坦演藝生涯的最后三十年中,他還曾對自己的演出做過這樣一些改革,他不事先宣布演出曲目,而是在聽眾坐定后才決定演奏哪些樂曲,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名望吸引聽眾,而不是作曲家的名字,這種隨機的演出方法,更凸顯出演奏者的重要性,而它也非常符合魯賓斯坦樂于嘗試不斷創新的個性。
從1900年12月1日第一次在柏林登臺到1976年5月31日倫敦的告別音樂會,魯賓斯坦讓本世紀鋼琴樂壇為之著迷。這位彈起琴來不慌不忙的矮胖男人有著歐洲波希米亞人的外貌和堅毅而豁達的性格,在黑檀木與象牙所構筑的王國中他是氣質迷人的紳士,是舉止優雅的大師。有些鋼琴家以個人化的風格橫掃鍵盤,魯賓斯坦卻只是彈奏鋼琴;有些鋼琴家只是將樂曲推向高潮,魯賓斯坦卻只是持續不斷地在琴鍵上演奏,他讓音樂里的每一刻都更加悅耳、更有說服力。他讓他的人生如此連綿不絕煥發出奪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