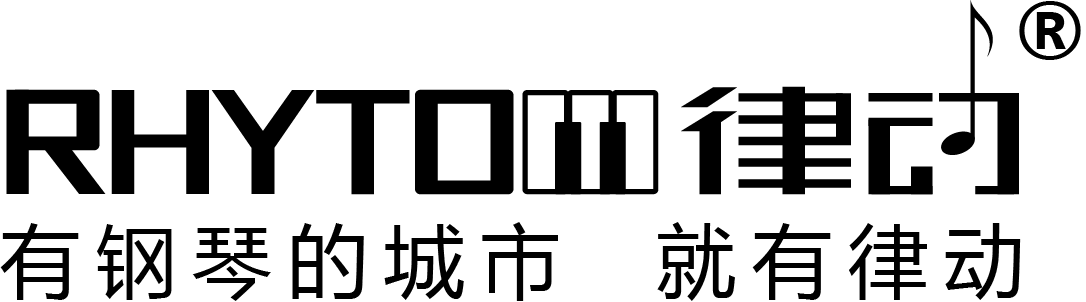她是令樂(lè)迷心疼的朱曉玫,“演出時(shí)披件圍巾是因?yàn)檠莩龇绨蛏掀屏藗€(gè)洞”;她也是令樂(lè)迷動(dòng)容的朱曉玫,“幾十年每天都彈巴赫,從沒(méi)厭倦,你每天吃飯會(huì)厭倦嗎”;她更是令樂(lè)迷尊敬的朱曉玫,“我已經(jīng)65歲了,如果有一天彈不動(dòng)了,我會(huì)悄悄離開(kāi),不再打擾大家”。她避世幾十年,不離不棄的只有鋼琴,這也是她召集信徒的武器,琴鍵一按下,不認(rèn)識(shí)她的人,都蜂擁而至,音樂(lè)會(huì)門票需要靠搶。神秘的大師,近日回到家鄉(xiāng)上海,終于破土而出。
隱士?
就在不遠(yuǎn)的“此前”,朱曉玫的名字,甚至在音樂(lè)專業(yè)圈內(nèi),都算陌生。然而,9日晚在上交新廳的獨(dú)奏音樂(lè)會(huì),門票被瘋搶得超越任何一位大師,臨時(shí)在13日加演一場(chǎng),更是在短短的10分鐘內(nèi),又被搶得一張不剩,門口的黃牛,甚至加價(jià)加到了幾千元一張。
吸引觀眾的,有她的傳奇經(jīng)歷。出生在上海,8歲就登臺(tái),卻遭遇文化大革命,隨后去海外,她的名字,跟傅聰、顧圣嬰等前輩大師聯(lián)系在一起。在她定居的巴黎,盡管1994年登臺(tái)后,只要她的演出,都爆滿,但她的生活,卻樸素異常,甚至沒(méi)有自己的房子—在發(fā)燒友小圈子內(nèi),她憑借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讓樂(lè)迷驚為天人,但在公眾面前,她卻是不折不扣的隱士。
“回國(guó)演出,有人要我講一些小故事,但我覺(jué)得,還是應(yīng)該少說(shuō),應(yīng)該用音樂(lè)來(lái)打動(dòng)觀眾。”昨天,她在接受滬上媒體訪問(wèn)時(shí)說(shuō)。她曾經(jīng)出過(guò)自傳《河流與她的秘密》,但為了不出這本自傳,她甚至請(qǐng)了律師,“當(dāng)時(shí),有出版商找到我,要我寫(xiě)自傳,逼了我三年,我不愿意寫(xiě)。最后,他們說(shuō),你實(shí)在不肯寫(xiě),那我們就自己寫(xiě)你的傳記了,我一聽(tīng)急了,怕他們亂寫(xiě),就請(qǐng)了律師,結(jié)果律師告訴我,我沒(méi)法阻止人家寫(xiě),最后我被逼上梁山,只能出自傳—很多悲慘的故事我沒(méi)寫(xiě),因?yàn)槲也幌肱煤芸嗲椤?rdquo;
讓她能夠忘掉那些痛苦的,是一架陪了她三十多年的鋼琴,即使在下放到張家口干農(nóng)活兒時(shí),她也在偷偷彈鋼琴。而在海外,她仍然每天都會(huì)彈巴赫,尤其是《哥德堡變奏曲》,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更成就了她隱士的傳奇。“巴赫是我最喜歡的音樂(lè)家,我"跟"了他三十多年了,他的作品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cái)富,對(duì)任何民族和宗教都有穿透力。”
苦行僧?
在國(guó)內(nèi)經(jīng)紀(jì)人請(qǐng)她回國(guó)巡演前,朱曉玫過(guò)著苦行僧的生活。一如她當(dāng)初拒絕出自傳一樣,她也曾拒絕回國(guó)演出:“結(jié)果他就說(shuō),可以等我,他還讓我想想,以后該怎么退休?他知道我連房子都沒(méi)有。”
不僅沒(méi)有房子,她也不看電視、電影,好朋友只有幾位作家,和“搞經(jīng)濟(jì)又拍電影的”。“朋友都說(shuō),朱曉玫除了彈琴就是個(gè)廢物,甚至不會(huì)用手機(jī)找路,”她自嘲,“不過(guò),我也不覺(jué)得自己是苦行僧。有人認(rèn)為這種生活很苦,覺(jué)得一百個(gè)人慶祝生日會(huì)很好,但我就覺(jué)得這是最痛苦的事—首先,生日有什么好慶祝的?其次,跟100人談話多累啊!”
所以,她只活在純粹的音樂(lè)里。讓她不安的,是“一個(gè)男孩子從湖南衡陽(yáng)來(lái),買了兩千多的票,加上差旅費(fèi),一個(gè)月工資全沒(méi)了,我很心疼,他們把我吹得太高了,捧得太高了,結(jié)果大家上當(dāng)受騙了”;讓她興奮的,是“上交新廳是我全世界彈了200多場(chǎng)聲音最好的,鋼琴也好,觀眾非常安靜,提問(wèn)都是專業(yè)級(jí)”;讓她憤怒的,是“來(lái)演出時(shí),門口黃牛來(lái)跟我推銷票子,我說(shuō)"你們?cè)趺茨茏鲞@種事呢",他們都嚇跑了,我覺(jué)得藝術(shù)為何總要跟錢掛鉤”。
所以,她穿著跟了她三十年的演出服來(lái)演出,拿塊披巾?yè)踝〖绨蛏系钠贫矗粸榱艘蝗缂韧貎?nèi)心平靜。